一
社会的某种巨大转折,总是悄无声息地进行。每当我们蓦然回首时,才发现自己乘坐的列车,离开那一处风景已经远了。
比如,手工业时代是什么时候结束的,不明确。等我们感觉生活方式有明显变化时,我们已经身处工业化时代了。
但也不是不存在衔接点。只不过被我们忽略了。细心回想,还是能发现一些迹象。比如,一些寻常至极的生活用品渐渐出现在民俗展览馆里;比如,体力劳动者双手上不再布满老茧。
如果以上迹象出现的时间仍嫌模糊,还有一个明确的标志,那就是自从城乡亿万双脚上穿的鞋子忽然变成了机制鞋。从那时开始,可以说手工业时代真正结束了。
时间说得再具体一点,大约就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,离现在不太远。
四十多年前,我第一次去四川,看到街头上那些品类繁多、制作精良的竹器时,并没有意识到,那是手工业时代的尾声。以后第二次、第三次再去,已经很少看到,取而代之的是琳琅满目的工业产品。
第一次徜徉在专卖竹器的商铺里,我惊叹竹子竟能编织出那么齐全的生活用品:床、凳、椅、篮、盘、筐、篓、罐、盒,还有扇子、筛子、爪滤、簸箕、蒸笼、斗笠……
最吸引人的是一套竹编沙发,由三人座、双人座、单人座以及一个长方形条几组成,十分雅致新颖。骨架当然是竹子,面料全用细如韭叶的竹篾精编密织而成。一问价钱,也不算太贵。如果不是考虑到青海干燥,竹器不宜,我真想把它买下来,托运回西宁。
我在这组沙发前久久流连。边看,边想象它的创作者。
他是耗费了多少时日,手持哪些工具,锲而不舍地锯、削、劈、凿、烤、刮、编、磨,才把山林中的青竹变成了这件大型家具兼工艺品?
我想象那双手一定是遍布老茧、伤痕累累,手指头和指甲缝时不时地被锐利的竹刺扎伤过。
二
在这个星球上,还没有任何物种进化如此完美的手(或者爪子):力量和技巧兼于一体而不抵牾。紧握成拳时,筋脉怒张,可以击打捶捣,断砖劈石;绽放开来时,巧妙组合,可以飞针走线,镌刻雕琢。
手工业时代,手的潜能得到了极大的开发。凭着27节骨头和与之配套的肌肉、筋腱,人的手有了足以让上帝赞叹的功能。
手工技术成熟之后,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从最初的实用性逐渐分离,出现了实用性和艺术观赏性兼而有之的产品,比如瓷器、铜器、刺绣、玉器、家具等。博物馆里那些巧夺天工的名贵玩意儿,机器是做不出来的。据说还有人曾在大米粒大小的象牙上雕出过一首唐诗。
而惊人的技巧总是被手的粗糙外表掩盖着。
我在德令哈生活时,到一位干部家串门,看到一张圆形小餐桌。桌面见不到巴掌大的一块木料,全用小如鲫鱼的菱形小木块,拼接成美丽图案。木块色泽各异,接缝细如发丝,精确至极。
这要经过多少次计算和削磨,才能做到!主人告诉我,匠人是个年轻木工,河南省鹤壁人。鹤壁自古出良匠嘛。
主人还告诉我,他在老家亲戚家里还见过一把粉彩小茶壶。茶壶上布满了铜铆钉。铆钉把许多小瓷片拼接起来,组成冰裂图案。这是有意把新茶壶打碎后,请当地手艺最好的匠人重新组装的。一点都不漏水。
我知道,这两位匠人是在炫技。炫技之外,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广告。
做手工活需要耐心。耐心是手工的灵魂。那个时代慢节奏的生活也有利于培养耐心。俗话说,慢工出细活。“良匠贵工不贵速”。没听说赶时间求进度能搞出好玩意的。
三
自从19世纪初,西方资本进入中国沿海市场,陆续开办工厂,手工业产品就逐渐被成本相对较低的工业品替代。这个替代过程很是漫长。但现代物质文明之风那时还吹不到西部边远地区。人们目之所及,手之所触,多是手工制品。一位成长于门源县仙米农村的朋友告诉我,他在13岁之前没见过玻璃器皿。家里用的碗,碟、盘子、勺子,全是就地取材用木头做的。
手工业时代,绝大多数人赖以谋生靠的就是双手。手的创造能力是生活环境逼出来的。
一个人,如果不在官吏士商之列,也非耕地种田之人,也非巫医优伶之属,亦非从军吃粮之辈,那就一定是匠人。除此而外,就是游手好闲之人。游手好闲这个成语或许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。而在现代工业化时代,“游手好闲”说明不了什么,一个人能不能创造价值,与手不一定有关系。
手工业时代,“匠人”这个称呼几乎涵盖一切“仰十指而食”的草民。除了生活中万不可缺少的四大匠人:木匠、铁匠、石匠、泥瓦匠之外,还有银匠、鞋匠、皮匠、擀毡匠、箍桶匠、饦笼匠(制作蒸馒头的蒸笼),碗儿匠(补锅钉碗)、油漆匠、画匠(为大型建筑敷彩髹漆、描绘花草;给家用面柜、米柜、衣箱、屏风作装饰画的人。)这类人一般都在重复传统图案,少有创新,故只能称之为画匠,而不是画家。此外,还有骟马匠、劁猪匠、影子匠(唱皮影戏者)。
“匠人”专业性强,一般来说串行或跳槽几乎不可能。
“匠”的分类法不但成为一种职业标签,甚至延伸为一种人性标签。在青海,人们把具有某种品性特征的人,也调侃地纳入“匠人”之列。比如,把夸夸其谈的人称为“赞匠”;把不知珍惜、随意损坏的人称为“整匠”;把喜好挥霍、不爱节俭的人称为“散(读第四声)匠”;把性子很肉、行动磨叽的人称为“冉匠”;把喜欢拿大话吓唬人的称为“唬匠”;把做事敷衍马虎的人称为“乱(读第一声)匠”。
可见“匠”这个称呼影响之大。
四
手工业时代人们活得辛苦。那些粗糙皴裂,骨节变形的手,一看就是匠人的手。2022年我回老家,一位曾经当过铁匠的亲戚来串门。喝茶时,我注意到他的手型粗大,与他中等偏低的身材不成比例。他也觉察到我在看他的手,就伸出来给我看,“你看看,铁匠的手。”
他问我:“你认为,在过去,铁匠和木匠谁的苦大?”
我说:“木匠苦大。别的不说,把大树锯倒、解成板材,全靠双人四只手拉大锯。湿木头夹锯子,干这活能把人挣死。”
他说:“拉大锯虽然苦大,但是实在拉不动了缓一口气还是成哩吧?铁匠呢?烧红的铁块放到砧子上,抡起铁锤就得不停地打,停不成!温度降得很快。我当学徒的时候,右胳膊肿了消、消了又肿。嗨,那个苦你不知道!”
但是,铁匠木匠固然苦大,百姓人家,谁的双手不辛苦?在自由生育的年代,一个家庭,如果有五六个以上的孩子,单是做鞋,母亲的十个指头就不够用。点灯熬油、见缝插针地做,还是赶不上孩子们对鞋的消耗。我等农村长大的人,太清楚做一双鞋程序之繁杂。春暖地酥,先在房前屋后寻找空地种植亚麻。秋天收割了,找个大坑用水泡上,叫作“沤麻”;沤好了,捞出来,晾至半干,开始剥麻;剥好了,手掌沾唾沫,搓成一把一把麻线备用。然后开箱发箧,找出破衣烂衫,拆了,铰成铺衬;然后打糨子,粘袼褙;然后铰鞋样,纳鞋底,绱鞋;绱好了,找楦头楦鞋,喷水,晒干定型。
无数母亲的眼睛就是油灯下做针线熬坏的;手指头就是纳鞋底纳得变形的。
进入工业化时代,母亲们告别了麻线、袼褙、锥子和顶针。双手得到了解放。除非忽然有了兴致,想重温一下自己的技艺。
小型电动工具的广泛使用,减轻了木匠之苦。木匠们也不约而同地学会了取巧,缩短了工时,节省了力气,爱护了双手。如今还有谁见过木质家具(包括高档家具)构件的结合是开榫挖卯,用文火熬制牛皮胶完成的吗?有谁见过写字台抽屉在木头轨道上滑行吗?早就没有了。前者用螺丝钉,后者用钢片。效果怎么样呢?我家里一套实木餐桌餐椅,是大品牌,觉得很放心。谁知只放心了几年。有一次请客吃饭,客人屁股底下突然“咔嚓”一声,吓人一跳。起身一看,椅背和托板的结合处张开了,再细看,才发现藏在隐蔽处的螺丝钉已经松动;再后来,一件结实的橡木三斗柜,抽屉滑轮好几次从钢片轨道上滑脱,抽屉卡在那里,拉不出来又推不进去。
而早年请木工做的斗柜,抽屉直到现在都是平出平进,从来不“栽跟头”。
五
手工业时代,产品没有质量监管部门。产品能否在市场立得住脚,全看质量和信誉。产品也没有统一形制,这有利于发挥创造者的个性。手工业时代的产品差不多都是“限量版”,极少重复。比如同样是餐具、茶具、桌椅,南北方风格大不一样。而到了工业化时代,批量生产的东西难免同类化。你在西藏某户人家的客厅里看到的红木家具,有可能在广东某宾馆里看到的是同一款式。
手工产品往往也是人们寄托情志的载体。我小时候曾见过家里有一方铜墨盒。盒盖上刻着两句铭文:“松烟不负右军字,狼毫偏爱东坡词”。(此物后来消失于收缴铜器支援工业建设的年代。)有一柄五边形的竹扇,至今还在。竹扇上留着父亲写的毛笔字。正面是“采自青竹,编自妙手”;背面是“轻摇生秋意,退暑又驱蝇”。我有时拿起这柄竹扇,想象着父亲写下这几行字时闲适的心态。
手工产品往往也是承载记忆的物件。清代诗人周寿昌直到到晚年还保存着一件旧布衫,因为那是母亲给他缝制的:
“卅载绨袍检犹存,领襟虽破却余温。重缝不忍轻移拆,上有慈亲针线痕。”
而如果是一件制衣厂生产的夹克衫,恐怕就存不住这种感情。
人的这种感情寄托倾向很牢固。有人至今还保留着一个小小的红泥火炉,只因为上面镌刻着一行字:“且待微雪时”。看到它,会想起和朋友冬日小酌的情景;有人还保留着一个称药的戥子,只因曾在药店抓药几十年,手底下有如神助,“一把抓”的外号闻名街衢,这杆戥子就是他的神技的见证。
但一般来说,人们不会去保留一部早已过时的“大哥大”手机,或一台老式电脑。因为它们不过是电器垃圾罢了。
六
随着科技进步,智能工具剥夺了手指锻炼的机会。现代人白皙的手指除了在键盘上灵活飞动,在实际生活中反而笨拙。工具越来越先进,很少需要用手指头来完成高难动作,依照“用进废退”的自然规律,手的功能渐渐退化。27节骨头以及相配套的筋腱显得有点多余。许多女性的纤纤玉手捏不住一枚绣花针。衣服扣子掉了,竟然也能把人难住。居家过日子,有时,不得不用刀子削个什么,或是用斧子劈个什么,同样也会让一个大男人费尽气力、把自家的手弄伤了仍不免失败。这要是被以前那些粗手大脚的匠人看见了,会嘲笑说:“看,手笨得跟脚一样!”
手真是笨得跟脚一样了。
我庆幸自己的手还经历过一些磨练,不算笨。回想那个时代,由于生活用具的极度匮乏,迫使自己制作一些小物件。在德令哈生活时,我曾用简单的几样工具,费老大功夫,做成了一个结实的小板凳;削出了一个挖米饭用的木勺;用12号铁丝和漆包线编出了一个捞饺子的爪滤;用半截废旧话筒杆制作了一个台灯,等等。
我常常自诩,在吃文字饭的人当中,我算是动手能力强的人。
但无论如何,工业产品替代手工产品,是伟大的进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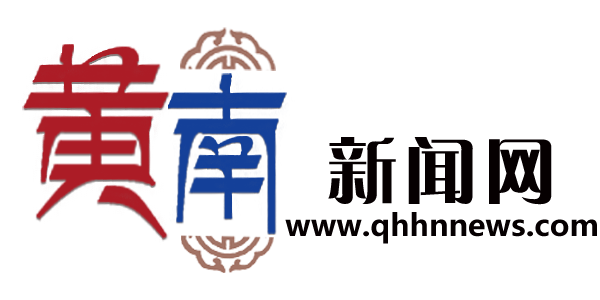

 青公网安备 63232102000018号
青公网安备 63232102000018号